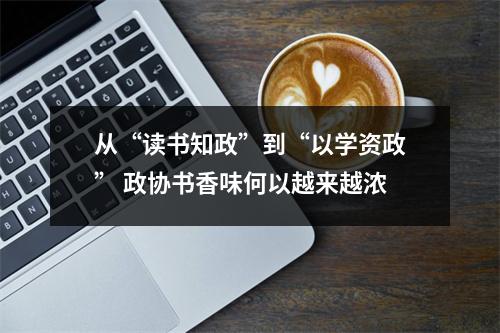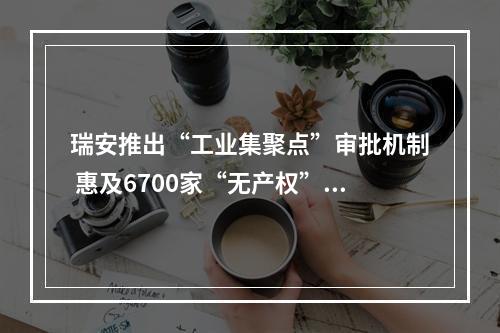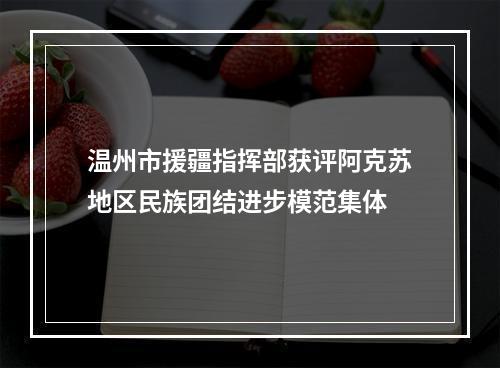王十朋塑像。
乐清梅溪村王十朋纪念馆。
温州网讯南宋大儒朱熹少年得志,比温籍大贤王十朋小18岁,但早9年中进士。王十朋与朱熹同为理学中人,同样坚持抗金,忠君爱国,政治主张相同,曾经同年同试临安,虽然无缘相见,但两人相互仰慕,情谊深厚。
通信推崇
隆兴二年(1164),王十朋知饶州,途经江西玉山县汪应辰的家乡,遂拜访汪,第一次写信给朱熹:“过玉山,邂逅侍郎汪丈,极口称道登时三札,所论天理人事,备数千言,高见远识,当于古人中求之也。”信中所称“侍郎汪丈”即汪应辰,为朱熹从表叔,与王十朋关系比较密切。“登时三札”指隆兴元年(1163)朱熹应诏入对,向宋孝宗面奏三札:一札论正心诚意、格物致知之学,反对老、佛异端之学;二札论外攘夷狄之复仇大义,反对和议;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,反对宠信佞臣。
乾道三年(1167),王十朋知湖州,得知湖州通判宋翔乃朱熹之“里闬交游”时,他致信朱熹,托宋翔转交,“盛有以称道”。王十朋年龄大于朱熹,官职高于朱熹,以一郡之长先驰信向赋闲在家的朱熹致意,显示出他对朱熹的敬重与赞赏。朱熹得知王十朋对自己的称誉,“辄敢复因宋倅相为介绍,致书下执事,以道其拳拳之诚”,写了1300多字的《与王龟龄》(王十朋),委托宋翔带回,向王十朋问候致意。
在回信中,朱熹对王十朋仕途生涯作出评论:“听于士大夫之论,听于舆人走卒之言,下至闾阎市里妇女儿童之聚,莫不曰‘天下之望,今有王公也。’”然后说读了王十朋廷试时的《御试策》、馆阁时的《奏疏》、台谏迁侍郎时的《谏章》、为故大丞相张浚所写的诔文,以及知饶州时编撰的《楚东酬唱集》等诗后,十分赞叹,“盖无一言一字不出天理人伦之大,而世俗所谓利害得丧、荣辱死生之变,无所入于其中。读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,鄙吝消落”,说自己能“不得一从宾客之后,以望大君子道德之余光也”。
朱熹还在回信中叹曰“明公之志,则正矣,大矣”,对王十朋的德望推崇备至。“明公以一身当四海士大夫军民一面之责,其一语一默、一动一静之间,所系亦不轻矣。”“况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,仅一二数。”朱熹对王十朋的政绩、为人、学识及思想的崇敬赞赏是无与伦比的,把王十朋的精神境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举荐奖誉
朱熹在不同场合对王十朋的人品、官品有盛誉。乾道三年(1167),刘珙除同知枢密院事,朱熹向刘珙投书举荐王十朋,提到:“今日之事,政须为其大者。论荐人材,亦有次第。今日远则益州(指汪应辰),近则吴兴(指王十朋),皆第一义谛,而敬夫(指张栻)尤不可后。”是年七月,王十朋由夔州移知湖州(吴兴)。
乾道四年(1168),朱熹在一封给弟子与学友何镐的信中说:“朝政比日前不侔矣,近又去一二近习,近臣之附丽者亦斥去之,但直道终未可行。王龟龄自夔府造朝,不得留,出知湖州,又不容而去。今汪帅来,且看又如何。上以荐者颇力,又熟察其所为,其眷伫少异于前矣。多然事系安危,未知竟如何耳。熹无似之踪不足为轻重,然亦俟此决之耳。”信中透露出朱熹对当时朝政直道不行之忧虑,反映出他期望朝政得以改观的心态,也流露出对刚肠直道的王十朋“不得留”的深深惋惜。
朱熹在为前辈傅自得所写的行状中写道:“泉州两税外复科,宗子来岁岁增广,民不堪命,郡太守若周公葵、王公十朋皆尝请罢之。”即泉州沿海等地官员从盐民那里多收取盐税(实物盐),然后卖掉以增加收入,贫弱盐民独受其害,周葵、王十朋曾经向上司申请停止这一做法。朱熹并且提到“太守之贤者,如宋公之才、王公十朋、周公葵皆高仰之,待以异礼,而公月不过一诣郡,每留语,谈说道谊而已。”可以看出,朱熹对王十朋任泉州太守时的政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,认为是贤太守。
乾道七年(1171),王十朋除太子詹事,专授太子治学之道。朱熹于淳熙十五年(1188)向孝宗上奏:“夫自王十朋、陈良翰之后,宫寮之选号为得人,而能称其职者,盖已鲜矣。”其奖誉王十朋之心态溢于言表。
讲学举例
朱熹在对其门生讲学时,曾多次讲到王十朋,对其个人修养和治政十分称赏。对当时一些为名利所牵的士大夫,朱熹是深表失望并予以批评,他对学生说,士大夫贪得患失“只是自家无志。若是有志底,自然牵引它不得。盖他气力大,如大鱼相似,看是甚网,都迸裂出去。才被这些子引动,便是元无气力底人。如张子韶、汪圣锡、王龟龄一样底人,如何牵得他。”他还对学生说过:“王龟龄奏议气象大。”《朱子语类》记载:“籍溪胡宪轮对,乞用张魏公、刘信叔、王龟龄、查元章,又一人继之。时有文集,谓之《四贤集》。”张魏公即张浚,刘信叔是刘锜,查元章即查籥。绍兴末年到乾道初年朝廷政事未好转,从朱熹对胡宪奏对之语的评述可见,朱熹亟盼政局改观,对张浚、王十朋等人抱有期望。
《朱子语类》还记载:“王龟龄学也粗疏,只是他天资高,意思诚悫,表里如一,所至州郡上下皆风动。而今难得此等人。”“王詹事守泉。初到任,会七邑宰,劝酒,历告之以爱民之意。出一绝云:‘九重天子爱民深,令尹宜怀恻怛心。今日黄堂一杯酒,使君端为庶民斟。’七邑宰皆为之感动。其为政甚严,而能以至诚感动人心,故吏民无不畏爱。去之日,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,公亦为之垂泪。至今泉人犹怀之如父母。”王十朋自幼精研六经,深谙儒家思想的精髓,撰写了“《春秋》《尚书》《论语》解”,朱熹从理学家的标准来评价一位并不专门研究理学的学者和政治家,不免认为王十朋在学术上显得有些“粗疏”,尚欠火候,但仍旧承认他“天资高”、为人忠诚、“表里如一”,在各地官民中声誉卓著,而像这样的官员十分难得。
题盖写序
乾道七年(1171),王十朋逝于左原故居。淳熙五年(1178),为纪念表彰王十朋一生尽忠爱民的功绩,汪应辰撰墓志铭,张栻书丹,朱熹题写碑盖,由于他们三人与王十朋皆是名臣贤士,后人称该墓碑为“四贤碑”。
淳熙五年(1178),刘珙知建康,当时王十朋的儿子闻诗以父恩监建康粮料院,正是刘珙的属下,拿出《王梅溪文集》请刘珙作序,刘珙因病请朱熹代作。接受代作序的任务后,日夜记挂,一天与好友刘玶等人酒醉而卧,半夜醒来后再也睡不着,感叹王十朋的为人处世和道德文章后,“忽得数十百言”,就立即起床点灯书写,心中对王十朋充满敬意。
朱熹代刘珙作的《王梅溪文集序》说王十朋是诸葛亮、杜甫、颜真卿、韩愈、范仲淹五君子后又一君子。“公始以诸生对策廷中,一日数万言,被遇太上皇帝(高宗),亲擢以冠多士,遂取其言施行之。及佐诸侯、入册府,事今上皇帝(孝宗)于初潜,又皆以忠言直节有所裨补。上亦雅敬信之,登极之初,即召以为侍御史,纳用其说。”“为数郡,布上恩,恤民隐,早夜孜孜,如饥渴嗜欲之切于己。去之日,民思之如父母。”其诗“浑厚质直,恳恻条畅,如其为人。不为浮靡之文,论事取极己意。然其规模宏阔,骨骼开张,出入变化,俊伟神速,世之尽力于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。其他片言半简,虽或出于脱口肄笔之余,亦无不以仁义忠孝为归,而皆出于肺腑之诚。”对王十朋文章赞誉有加,认为其文气势宏阔,而且是基于其人品之上。“盖其所禀于天者,纯乎阳德刚明之气,是以其心光明正大,疏畅洞达,无有隐蔽,而见于事业文章者一皆如此。海内有志之士,闻其名,诵其言,观其行而得其心,无不敛衽心服。”“呜呼!公之必为君子,盖不待孔、孟、尧、舜而知之矣。”“在朝廷则以犯颜极谏为忠,仕州县则以勤事爱民为职,内外交修,不遗余力,使君德日跻于上,民生日遂于下,国步安强,隐然真有恢复之势,则公虽云亡,而其精爽之可畏者为无所憾于九原矣。”言王十朋虽去世,但其精神永存。
来源:温州日报
原标题:同道君子惺惺相惜——王十朋与朱熹的交谊
作者:赵顺招/文王强/摄